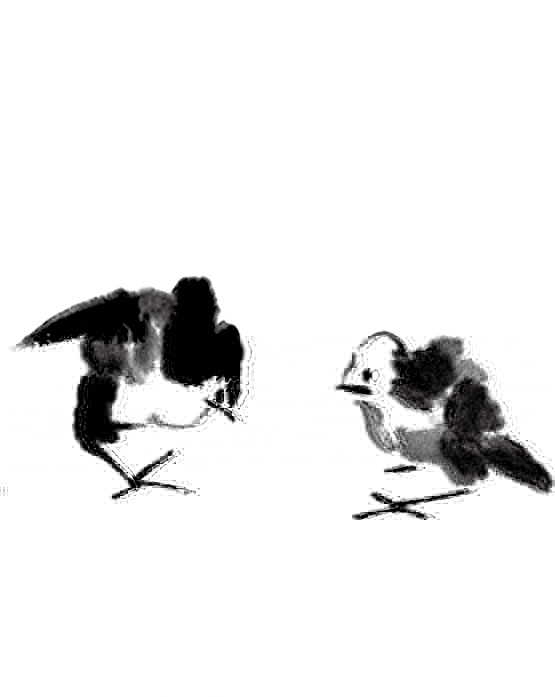《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
《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
——以《老子》首句为例探讨“道”之英译问题
章媛
《老子》在西方广为流传,依据沃尔夫(Knut Walf)教授的最新统计,西《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译文本有643种之多,涉及31种语言,其中英译有206种。“道可道,非常道”作为老子五千言开篇论道首句,体现全文主旨。此句仅六字,却出现三个“道”字,从句式结构、语法功能方面看:第一个“道”是名词主语,第二个“道”是动词作谓语,第三个“道”是名词宾语;逗号前的句子是主谓结构,逗号后的句子以前句所指为主语部分,其本身是谓语部分,由名词担任。可以说译者是否正确领会《老子》,第一句“道”字的翻译显得十分关键。但深究这些译本,不难发现译者翻译时对老子之“道”存在内涵缺失,对“可道”之“道”存在句法失误,对“常道”之“道”存在文化丢失。本文以世传本“道可道,非常道”为英译本的底本,以所收集到的近200种译本为蓝本,分别通过译本与《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原文的比较、译本之间的比较,以及选词、句式的变化,探讨英《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译文本之谬误及原因,进而论述跨文化翻译传播须力戒误译误释,译者既要忠实《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原文,更要尊重《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原文化。
一 “大道”如何归本——译本首个“道”概念迷失及修正
“道可道,非常道”统揽全篇,直指主题,句式隽永,含义丰盈,包含了“道”既可以是形而上的哲学所指(常道),也可以是形而下的实存(可道之道);既指出了可道之道与常道的区别,又分开了老子之“大道”与世俗之道的界限。译者选择什么样的词来翻译老子开篇之“道”,既体现了他们对《老子》的理解程度,又体现了他们的跨文化传播观念,甚至决定着译本的学术价值。老子之“道”寓意究竟何在?《庄子·渔夫篇》曰:“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则道为万有之根源,乃道体之“道”。依河上公、王弼注:第一个“道”字,通名也,指一般之道理。
老子之“道”内涵深刻,外延无穷,如此之“道”,老子称之为“大道”。对此,译者是如何发掘目的语中的对等概念来选词翻译,根据笔者对百余种英文译本统计,首个“道”的英文本主要有如下选词:“principle”、“road”、“truth”、“teaching”、“spirit”、“Cosmic Consciousness”、“the Ineffable”、“path”、“direction”、“infinity”、“Atheism”、“N(n)ature”、“W(w)ay”、“T(t)ao”等等,其中尤以Way,Nature和Tao占绝大多数。下面就以这三个英文词汇为重点,分析译者对老子之“道”的追寻及得失,并阐释其文化根源。
1. Way译“道”的宗教性
虽然不像选用God(上帝)、Logos(逻各斯)、Word(上帝之言)、Reason(理性,第一原因)、Creator(世界创造者)等词那样用上帝的代名词来译“道”直接,但用Way译“道”更具有宗教概念转移的隐藏性。在统计的百余种译本中,有大约四分之一的译者选用Way来译“道”,有的用大写的Way,有的则用小写的way,有的在其前用定冠词the,有的用不定冠词a。这其中包括像亚瑟·韦利(Arthur Waley)、梅维恒(Victor H. Mair)、韩禄伯(Robert Henricks)等深受读者欢迎的译者,他们的译本在西方多次重印。把老子的“道”译为(the/a)Way或(the/a)way,表面上看义近词同,但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其中所含的深刻的基督教根源,因为在《新约》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就有这样的对话:
耶稣:“You know the way to the place where I am going.”(你们知道我将去的路。)
门徒:“Lord,we don’t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so how can we know the way?”(主啊,我们不知道你要去哪里,怎么能知道你要去的路呢?)
耶稣:“I a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life.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me.”(我就是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由此可见,Way在西方已成一个家喻户晓的、含有基督意义的专有名词,只要一提起它,西方人第一印象就会想到“上帝之路”,而这个道路没有耶稣基督的帮助无以达成,所以耶稣是连接上帝的通途。译者从《老子》里读出了通向上帝之路——the Way,正是译者这种基督文化“本位性”的体现。亚瑟·韦利(Arthur Waley)选择用大写的“Way”译“道”,他的第一句《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译文“The Way that can be told of is not an Unvarying Way”,让人很自然地联想起耶稣的活:“I am the Way and the truth…”罗伯特·威尔金森为韦利的译本所撰写的序言中明确指出“the Way”具有基督色彩,他说:“译本中的Way很显然是基督思想中同一个词的类推。”
其次在身为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的布莱克尼(R.B.Blakney)译本中,也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之所以用Way译“道”,是因为Way与“上帝”的概念相符。另外,能与Way相媲美的词则是Logos和Word(言语)。
从选用way译“道”的译者的思考可以看出这样的问题,首先他们对老子“道”有比附《圣经》中耶稣的倾向,其次又借助老子之“道”在原语中有“道路”或者“人的行为方式”等意义,使《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译文表面上更接近原语。实际上,是把具有深刻基督文化内涵的“Way”巧妙地隐藏在看似可以与原语对接的选词当中,这既避免了直接译为“God”等词的生硬、牵强,又达到了文化概念的偷梁换柱,可谓用心良苦。
2. Nature译“道”的局限性
用Nature译“道”的译者着重把老子之“道”定义为“自然而然”和自然的总原则。巴尔福(Frederic Henry Balfour)在其译本《道家著作:伦理、政治和思辨》中,分析指出了用Reason和Way来翻译“道”都不能表达“道”的确切意思,相较而言,他认为principles或者principle of nature比较合适。因为在他看来,老子之“道”是“花儿自开,水自流,日月星辰各自行,红发黑发人自长,所以老子之‘道’即为自然(Nature),或自然之法则(the principle of nature)”。巴尔福进而指出,这里的自然不光是物理方面的自然,还包括人类,人类被认为是赋予自然的最直接的礼物,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与其说巴尔福把“道”翻译为“自然”,倒不如说是把它翻译为“自然的总原则”。
对巴尔福用Nature译“道”,同时代的理雅各(James Legge)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巴尔福不过是借用了哈德威克(Hardwick)对“道”的翻译,并且根据他所解释的意义理解“自然”——上帝是总的原因和指挥者。因为Nature可以为Way(自然之法),可以为reason(道理),可以为teaching(教理)。理雅各在其《道家经籍》中指出:“如果用Nature译‘道’果真如巴氏解释的那样,涵盖了这许多意义,那么他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这种译法。”但他又指出,巴尔福理解的“道”既重在自然之理,却又把非自然的东西加进去,只能惑人心智,使老子的思想更加让人迷离。此外,翟林奈(Lionel Giles)也坚决反对巴尔福的观点。翟氏在其译本《老子箴言》中对“道”的先验性特点描述时,发现老子的论述是证明“道”的先验性特点在物质方面得到显现,因此很难用一个合适的词表达其哲学概念。
由此可见,用Nature译“道”,即使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西方译者之间都不能达成一致,说明《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译文对《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原文的意涵丢失现象已显露无遗。也有较少译者选用如teaching、path、ineffable等词来翻译,但他们彼此都不能说服,更不要说翻译老子之“道”既是本体的形而上之根本又是形而下之万物,既有“非在”又有“此在”的哲学内涵,岂是一个区区的Nature或其他个别译词所能指称?
3. Tao译“道”的“无译性”
在笔者收集统计的百余种《老子》英译本中,用Tao音译老子之“道”的占了一大半,有62人之多,可见译者们已逐渐达成了一致:首先他们明白了老子之“道”正如古希腊的“逻各斯”、印度的“佛陀”一样,是属于中国文化特有的概念或思想体系或哲学范畴,因而老子之“道”就不是任何一个英文名词、概念或者意义所能取代的。
音译的“Tao”果真能译介老子之“道”吗?或者能算得上是翻译?其实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常常会碰到“译过”或“不足”的问题,当这种翻译的“欠额”或“虚值”太大,“硬译”必然影响读者的理解,甚至产生误解。为避免这种“硬译”而产生的“过与不足”的问题,就经常会用到音译。具体到老子之“道”来说,就连他本人也说:“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再统揽《老子》全文可发现,这个“道”是“一”抑或“万物”,是“无”抑或“有”,是白抑或黑,是本体抑或实体,是变化抑或过程……“道”的这种周遍无限、全息全能性,决定其无法找到合适的概念性词语来界定翻译。
此外,文本的翻译与否及正确与否虽有很多标准,如严复提出的“信达雅”,鲁迅的“宁信而勿顺”,以及奈达提出的“动态对等”——即“以《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译文读者的反应与《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原文读者的反应加以比较”来衡量翻译的标准等等,但是核心只有一个即要忠实于《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原文。如果对“道”的翻译体现不出“信”或“动态对等”,那就只能造成“误译”。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就当灵活变通。按照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译者在翻译老子之“道”时就应当思考,这个“道”在《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原文本中是否也为读者留下大量的“空白”和想象空间?如果有,那么又何妨把这种《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原文本对应的效果也留在译入语中?事实正是如此,中文读者对“道”的理解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样采取音译,实际上就是对翻译学中最基本、最核心的“信”的理念尊重与实施。如果套用老子的话来说,这种音译体现出了“无译性”——无译而无不译。
综上所述,虽然不能说音译“道”就是最佳翻译,但“实译”则是“误译”。因此,在现当代的英汉语境下,与其误译而产生误解,不如音译为上,因为其他任何一个词都无法吃透与表现作为老子最高的哲学范畴“道”的内涵与外延的无穷性与丰富性。正如巴尔福所说:“任何一个翻译‘(老子之)道’的词都是一个‘道’的杀手,因为一旦‘道’被某个词翻译,那么‘道’所表达的其他意思就全被抹杀了。”(注:Frederic Henry Balfour,“Taoist Texts:Ethical.” Political,and 《牛津哲学辞典》等都把Tao作为专用词汇来加以定义与解释。
二 “可道”能否归真——译本第二个“道”的语法病句
朱熹曰:“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可道”犹云“可言”,在此作谓语;而据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注:第二个“道”字,指言说的意思。
但从句法结构而言,汉英两种语言的翻译体现了“可道”二字的复杂性。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汉语“道可道”的“可道”是谓语部分,由情态动词+谓语动词构成,意思是“道是可以说的”或者“道是可以被说的”。与目的语相比,原语的主动句式还可以表示被动。其次,“非常道”意思是“(可以被说的道)不是常道”。这句汉语的主语是承前省略。最后,从整个句子来看,“道可道,非常道”实际上是转折关系的并列句,意思是:道是可以说的,但是可以说的道不是常道。正是由于第二个“道”在这里体现出句法上的复杂性,西方译本只是从表层领会词义,而忽略了汉语句式架构的触类旁通,译本产生多种在句法结构上的歧途,大体说来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 “可道”谓语部分可否译为定语从句?
在统计的百余种译本中,90%的英译本都把第二个“道”译为“可以言说的”,或“可以表达的”,或“可以描述的”,或“可以谈论的”,或“可以被理解的”,等等。典型的《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译文如“Tao(The Way)that can be talked about”,其他《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译文或把“that can be talked about”替换为“that can be voiced”(Tao Huang,2005),或替换为“that can be spoken of”(Ren Jiyu,1985,John Dicus,2002,Tim Chilcott,2005);“that can be put in words”(Keith H. Seddon,2008);“that can be spelled out”(Lok Sang Ho,2002);“that can be expressed”(C.Spurgeon Medhurst,1905,Isabella Mears,1916,Herman Ould,1946);“that can be spoken”(Aalar Fex,2006,Derek Lin,2006);“that can be told of”(Lin Yutang,1955,Arthur Waley,1934);等等。这样,“道可道,非常道”就被译为一句话,回译成汉语就成为“可以说的道不是常道”。目的语的这句话显然丢掉了原语中的前半部分句意,即与前半句“道是可以说的”相比,强调“道”的可道性,而不是只能做定语帮助说明后一句话的意思。这种翻译显然是不恰当的。
2. “道可道,非常道”的并列结构如何体现?
少数译者考虑到了原语句式情况,没有随大流,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用了和原语近似的句式,把第二个“道”译作动词,这其中有把它作为目的语条件句谓语部分,如:“If Tao can be described,then it is not general Tao”(Thomas Z. Zhang,2004);“If Tao can be Taoed,it’s not Tao”(Herrymon Maurer,1985)。目的语以“条件句+主句”译原语的并列句,似乎靠近原意,但是条件句把原语句的外延限定了,它既没有译出原语的前半部分句意,反而把后半部分的句意更加缩小了,试比较“可以说的道不是常道”和“如果道可以说的话,它就不是常道”之间的差别。老子的意思是“道是可以说的”,这是肯定,然而在定语从句中却没有肯定这层意思,只是假设道可以说,合为主语的一部分。
鉴于以上问题,也有译者把它直接翻译为主句中的谓语,如:“The Tao can be explained,but this is not the real Tao”(Roderic & Amy M.Sorrell,2003);“The DAO can be talked about,but that is not the ever-lasting DAO”(Xiaolin Yang,2006);“The TAO,or Principle of Nature,may be discussed”[by all];“it is not the popular or common Tao”(Frederic Henry Balfour,1884)。这样的翻译看起来符合原语文本的句式结构,但在目的语中是否达到了与原语同样的接受效果呢?下面以刘殿爵的《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译文为例,来看这样的翻译是否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
刘殿爵(D.C.Lau)1963年首次出版自己的《老子》译本,由于受欢迎而重印再版了10多次。1982年,他根据帛书本又重新做了翻译。这次他把前译本中“The Way that can be told is not the constant way”句式改成“The Way can be spoken of,but it will not be the constant way”,使之成为与汉语相当的句式即并列句。1984年韩禄伯针对刘殿爵这个新译本做了书评。韩禄伯认为刘殿爵的第一句翻译有问题,他说:“‘The way can be spoken of,But it will not be the constant way.’是一个并列句翻译,回译汉语:道(1)可道也,(2)非常道也。如果(1)(2)是并列同等的谓语,那么就推导出‘The way is not the constant way’。这是很奇怪的。所以他仍然坚持:X(名称短语)也,非Y也。”根据韩禄伯的阐释,这样的翻译产生了严重的逻辑混乱。表面上看,目的语译本句式符合原语的句式,但事实上这只是硬译,译者没有根据目的语的语境和逻辑思维习惯去处理《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译文,只是一味追求形式上的统一,结果使目的语读者对此难以理解,甚至产生抵牾。韩禄伯的评论和观点还有待讨论,然而产生如此多问题的译本说明离“信”的要求还很远,要达到奈达“动态对等”的原则还有很多工作亟待完成。
3. “道可道”同源宾语如何译?
“道可道,非常道”中,动词的“道”和其主语“道”是逻辑上的同源宾语关系,有的《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译文考虑到了这层关系,如“Tao can be taoed”(Herrymon Maurer,1985);“No Tao that may be Tao”(Ha Poong Kim,2003);“To guide what can be guided”(Chad Hansen,2004);“The Reason that can be reasoned”(D.T.Suzuki & Paul Carus,1913)等,仍然保留了原语中这种关系。但问题是,这些译者为了使《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译文符合《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原文的同源宾语句式,在音译Tao(道)名词的基础上又创造了tao的动词。这样的tao势必规则不一,出现了上文的被动语态既可以是taoed也可以是tao,这就让《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译文的读者既诧异又难于理解。更有甚者,有的译者试图在目的语中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找到了如tread(踩)这样的词与原语“道”来搭配,结果《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译文就成了“The Tao is that on which one can always tread”、“The Tao that can be trodden”。这样《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译文大概只有译者才看得懂,或者懂得两种语言(原语和目的语)的人才能明白《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译文的意思,因为这里音译的Tao已经预设它在目的语读者中被明白了,而且是“道路”的意思——因为只有道路才能被“踩”。因此,要想这样的搭配为目的语读者普遍接受理解,可谓是难上加难。如“A way that can be walked”(Jonathan Star,2001)、“A path fit to travel”(Bradford Hatcher,2005)的《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译文,从英文字面上看,这种翻译似乎更接近汉语,然而这种英文搭配,在英文里的确是令人啼笑皆非的。Way(方法)如何被walk(走)?path(小径)如何被travel(旅行)?正如tao(总原则)被tread(践踏)一样。
可见,翻译要想贴近《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原文,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性工程,从选词、到句式、到修辞都要尽量无限地接近《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原文。《老子》本身内涵丰富,对那些惜墨如金的格言警句,译者在考虑如何译出句意的同时,一定得考虑是否丢掉了部分内容,否则“丢此加彼”就会直接影响或误导目的语的读者。
三 “常道”是否对等——译本第三个“道”的文化丢失
《韩非子·解老》有言:“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唯夫与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谓‘常’,言恒久不变也。”
老子之“道”是天地之理,宇宙之法,是一切存在的本根。然而“包罗世界万物及其规律的‘常道’,是不可如此明确分析名说的,这种可以分析名说的道,乃是人们可以感受得到的所谓养生、经国、政教之道。老子多处用‘水’的自然特性来晓谕道性,不仅阐明了道的柔弱、就下和应时达变特征,而且表明‘常道’乃是无法用语言进行符号化描述的一种存在,它是宇宙间永恒的大道,它只能由人们自己去体验,去感受。”老子之“常道”乃永恒之道,而可以眼见、可以分析的道乃是永恒之道的显现。恒常之道即恒久永远之道,是不变,然而这种不变不是具体事物之一成不变,而是指永远处在永恒不变之中的“永远变化”之规律,即“道法自然”。自然之法相依相克,万物自生、自化、自成、自灭,生生不息,循环往复。
《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译文“常”的选词主要有:“Constant”,“Eternal”,“unchanging”,“unvarying”,“perennial”,“Everlasting”,“permanent”,“changeless”,“fixed”,“enduring and unchanging”,“lasting”,“Immortal”,“absolute”,“Ultimate”,“primal”,“or cosmic”,“infinite”,“entire”,“ever-abiding”,“popular or common”,“general”,“true”,“all-embracing”,“universal and eternal”等。下面分类阐释,探讨其是否符合文本的原意。
1. “常道之恒久”如何译
在统计的百余种译本中,选择译词“eternal”的译者多达33人,其次用“constant”的译者9人,选择其他译词多在1~3名译者之间。这些词能否表达“恒久”(见表1)?
表1
。
从这几个词的意义即可看出译者在理解“常道”之时,好比盲人摸象,揣摩到什么样的意义,也就认为那就是老子之“道”(象)。然而,老子之“道”既不只是译者所感觉到的“道(象)”的某一部分,也不只是他们所感觉到的所有部分的叠加,老子之“道”乃是一个无以用语言表达的,任何具体的所指都同时否定了它不可指的另一面,这就是语言的局限性。
老子的“常道”,是超越的哲学。《老子》第一章第一句是概括,统领全文,而第25章是对第1章的阐述,也是对“道”的具体的说明。在笔者看来,老子在这里至少就他的“道”阐释了五层意思:一是“道”乃天地之根本,万物之母;二是“道”混沌无分别,浑然一体,没有名称可以命名;三是勉强给个名称的“道”,绝对不能完全表达老子心中之“道”;四是无声无形之“道”存于域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循环往复,无始无终;五是域中四大,人地天道依次效法,而道则归于自然而然之本体。仔细观察以上五点,前两个描述的是本体之“道”,属于形而上的范畴,后两个表述的是实体之“道”,属于形而下的范畴,中间的一个“强为之名”把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道”紧紧相连,从而构成了老子完美之“道”。这就是老子之“道”的高度哲学性或文化性所在。
对比汉语《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注释与英文选词,可见汉语的“常”是种,英文的选词是属,它们分别只包含其中的部分含义,所以以上的选词一方面只译出了《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原文“常”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却抑制了对“道”的其他性征的体悟。这说明《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原文本与译本之间存在着某些文化背景的差异,使译本丢失了文本原有文化含义,造成了二者之间的不可通透性。
结语
《老子》译本及译语之多堪与《圣经》相提并论,可谓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传播的瑰宝。然而,其《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译文与《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原文的差距以及译本之间的差异,却是《圣经》译本不能相比的,也可以说:世界上对任何一部经典著作的翻译所产生与《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原文的差异都不能与《老子》相比。无论从核心概念的翻译,还是对其固有的文化内涵的理解,甚至是句法结构的把握,西《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译文本都有大量的谬误。究其原因,除了客观上的中西文化背景与思维习惯的差异,亦有主观上的原因,自近代以来的中西跨文化传播中,中国文化在西方的翻译流传,一开始就缺少主动性,更无话语权。这样,带有西方文化背景的译者在翻译《老子》时有意无意地戴上了“色镜”,给原本白炽的道家文化加上了不该有的颜色,为译者自己或特定的读者群“把玩”和“欣赏”。这造成《老子》越来越多译本,质量不但没有增加,问题却不断增多,甚至达到了目不忍睹的地步。然而仅凭一篇文章,甚至一本书,是难以列举与校正其中的种种谬误。故本文只从《老子》开篇第一句,从选词到语法进行分析比较,指出译本和《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与诠释原文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误译所在,以求窥一斑而见全豹;同时希望引起学界重视,有更多的同仁来进一步分析《老子》误译误传问题,对中国传统经典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进行系统梳理,剔除糟粕,使中华文化为世人所真正理解,从而赢得尊重。这就是本文立意的初衷,抛砖引玉,恳请方家指正。
(作者单位:合肥师范学院外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