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黎--- 哪一位诗人不想当『玩童』
陈黎
哪一位诗人不想当『玩童』

陈黎
诗人陈黎1954年生于台湾花莲,20世纪70年代开始写诗。长达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里,他在台湾地区出版的诗集包括《庙前》《动物摇篮曲》《小丑毕费的恋歌》《家庭之旅》《小宇宙:现代俳句100首》《岛屿边缘》《猫对镜》《苦恼与自由的平均律》等十四部。
2015年,我在台湾花莲参加“杨牧文学研究会”时,又见陈黎老师。他热情相赠《轻/慢》《陈黎诗集Ⅰ》《陈黎诗集Ⅱ》《陈黎诗集Ⅲ》《跨世纪诗选》《想象花莲》等多部诗集、散文集。会议期间,夜间无事,便待在房间读诗。作为大陆的诗歌研究者之一,在阅读这些诗集之前,对这位诗人的印象无例外地流于刻板化,即《腹语课》《战争交响曲》《不卷舌运动》等音像诗呈现出的明显的语言游戏。事实上,陈黎确实追求“新奇”,这大概与台湾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整体努力方向有关。但求新求奇,并不意味着一切尝试都指向语言本体。他聚焦于汉语迸发出的奇思妙想,同样展现出无所不能入诗的奇特景观。无论是城市街道、历史古迹、宗教文明、神话故事、日常生活,还是工具书、旅游志、新闻报道、音乐戏剧、语言文字,都可以成为他写作的对象。因为熟悉多国、多地区的语言,接触不同类型的音乐,又深受不同诗歌前辈的影响,他的诗歌似乎别有洞天,语词与语词、诗行与诗行、标点与标点之间总能织补出新的曲式和音调。我在惊异于他对语言文字的灵敏、对音乐形式的自律之外,更为他持之以恒的“尝试心”所折服。
撇开研究者的身份而作为普通读者,在我看来,陈黎诗歌的动人之处就在于——“从一颗心荒废的杏核里重新回味”——每一寸疼痛的光阴都能够激荡出新的生命力:“牙痛与新月一夜阵阵增辉/老妪枯指下少女的琴音流泻/病后的宇宙坩埚,绿豆稀饭上/一点点细砂糖:足够甜蜜。”这是衰朽与狂喜、苦涩与甘甜的交响乐。2011年他患有手疾,牵及脚伤、心忧和视衰,他几乎不能用电脑创作。在病痛中,那些文字拼图好像高度兴奋的化学分子,互相缠绕、结合又分离,总是在他的头脑里活跃。语言文字形式结出的奇异果实,制造出独特的声音效果,渗透于他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既是朝夕相伴的快乐精灵,也是苦难疾病之河里抓住的一根稻草,将他送往生命的伊甸园。
对大陆读者而言,因为翻译聂鲁达、辛波斯卡等,陈黎的译者身份被普遍接受。但作为诗人,却刚刚进入他们的视线。这些年,我所接触到的诗人陈黎,思维高度运转,走路行色匆忙,穿着人字拖参加各类诗歌活动。看似不拘小节,但对文字的“计较”却令人发指。《蓝色一百击》《小宇宙》《跨世纪诗选》等诗集相继在大陆出版,想必读者会逐渐理解他为何会说:“哪一位诗人不想当‘玩童’?”那其中“玩”的深意,绝不仅限于语言游戏。我想,他是玩出了“新诗界”。
翟月琴:您的母亲通客家话。父母都讲闽南语,日常交流以日语为主。在台湾师大读外文系时,第二外语又是西班牙语。多种语言的生活和学习背景,为您日后的写作带来了什么影响?
陈 黎:中文(普通话)、闽南语、客家话、日语是我从小在台湾日常生活里,经常说或听到的语言,加上耳边有时流转的阿美族和泰雅族朋友的原住民语,自己求学时所习的英语和西班牙语——多语喧哗的情境,的确让我在写作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挪用中文以外其他语言的某些语汇,增加自己文字的趣味,或者帮助自己跳脱习惯的思路,迸出一些较鲜活的想象。
翟月琴:请问什么样的训练或成长背景对您的文化心灵影响最大?
陈 黎:在台北读师范大学英语系时,我透过原文或翻译,开始阅读许多外国诗人的诗作,包括叶芝(Yeats)、艾略特(Eliot)、罗宾逊(E. A. Robinson)、惠特曼(Whitman)、金斯堡(Ginsberg)、史蒂文斯(Stevens)、里尔克(Rilke)、波德莱尔(Baudelaire)、兰波(Rimbaud)……以及某些日本俳句诗人。身为英语系学生,我像台湾很多作者一样,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譬如罗宾逊,他诗中的悲悯情怀,激发我创作了一些以小人物为主轴的诗作;譬如艾略特,他的诗作《荒原》(The Waste Land)对于20世纪文学有十分深远的影响,艾略特带着批判和怀疑的眼光审视西方文明社会,以“荒原”象征战后文明表层下枯竭的精神层面,进而探索救赎的可能。我想我在诗集《庙前》里有一些作品多少受到了他的启发,譬如说《旱道》。艾略特的诗作激发我于1974年2月写下《旱道》这首诗。“旱道”两字一如“荒原”,用以指涉生命的平原的贫瘠干旱。我在诗前引用了艾略特另一首诗《普罗弗洛克的情歌》(“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的诗句:“We have lingered in the chambers of the sea/By sea-girls wreathed with seaweed red and brown/Till human voices wake us, and we drown.”(穆旦译:我们留连于大海的宫室,/被海妖以红的和棕的海草装饰,/一旦被人声唤醒,我们就淹死。)这首诗写的是一个人要跟女朋友见面,心中却老是被其他想做的事情盘踞,艾略特想借诗中人缺乏成熟的行动力,影射现代人行动能力的分崩离析,经常被心中所想象的事物所绑架,因为生命一片干旱,海中美丽的女妖听到人声便会散去,如同海市蜃楼一般,海中美景转眼便成虚幻,溺毙在想象的荒原中。艾略特诗中的意象对我有所启发,我当时也企图借由花莲这样的介于山海之间、富于母性的湿润的空间,去反衬孤寂荒谬的都会生活。又譬如金斯堡,他那首1959年写成,火箭似的投射出来,长句、无标点,开放形式的《怒吼》[1](“Howl”),触发我在1975年写出《李尔王》这首诗。
我在大学时代强烈地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阅读蛮多的西方文学作品,受到西方文学想象的熏陶;大学毕业之后,我试着通过英语和西班牙语翻译西方作品。我在写作诗集《动物摇篮曲》(1980)前后就注意到拉丁美洲文学,并且开始做译介的工作。大学毕业后我和我太太张芬龄一起翻译了许多外国诗人的诗作,例如拉金(Philip Larkin)、休斯(Ted Hughes)、普拉斯(Sylvia Plath)、希尼(Seamus Heaney)、沙克丝(Nelly Sachs)、巴列霍(César Vallejo)、聂鲁达(Pablo Neruda)、帕斯(Octavio Paz)、辛波斯卡(Wislawa Szymborska)——他们都影响了我。其中,聂鲁达的影响似乎更明显,因为我们至少译了四册他的诗集或诗选。
高中时我就喜欢听音乐,作曲家如巴托克(Bartok)、德彪西(Debussy),很早就影响启发了我。后来,韦伯恩(Webern)、雅纳契克(Janacek)、梅湘(Messiaen)、贝里欧(Berio)……也成为我的最爱。上了大学后,从画册里我接触了许多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抽象表现主义等画家的画作(譬如毕加索[Picasso]、布拉克[Braque]、达利[Dali]、马格利特[Magritte]、恩索尔[Ensor]、柯科西卡[Kokoschka]),他们也影响了我的美学经验。大学时图书馆管理员送我一本过期的《芝加哥评论》——1967年9月出版的“图像诗专号”——让我印象深刻,对我后来创作图像诗或许有些影响。
翟月琴:长久居住在花莲这一非都会区,您如何认知世界?
陈 黎:对我来讲,大胆/保守、通俗/前卫,岛屿/世界,似乎都是一线之隔。有人说我大胆,但其实我是保守的,从小到大读书循规蹈矩,名列前茅。有人看我下笔很快,创作加上翻译,作品近五十本,似乎活力充沛,不受拘束,其实我成篇很慢,一改再改,一想再想。但为什么我说自己不是大胆的人呢?因为我的举止、思想,从小就被书上读到的那些古圣先贤格式化了。孟子说:“说大人,则藐之。”又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或者“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些话非常潇洒,充满浩然之气,就像竹林七贤的行径,从小就影响我。七贤把天地放在内裤中,胸襟十分开阔。所以我不是大胆,而是向前人学习而来的。到过我家的人会以为我开录像带出租店,因为我有好几千片CD及DVD,听这些片子、看这些片子的时间都不够了,怎么还有时间出远门?我经常想人生有限,可以做些什么事,所以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在岛屿边缘花莲阅读、写作、翻译,俯仰宇宙,自得其乐。
翟月琴:您的《腹语课》《战争交响曲》和《不卷舌运动》是读者最熟悉的诗篇。因为语词环绕出的图像和音响效果,甚至被贴上“陈黎体”的标签。焦桐称您的诗为“前卫诗的形式游戏”,孟樊又谈到您诗歌的“语音游戏”。您擅长书写图像诗,对文字游戏情有独钟。或许诗歌本身就是一种游戏,您从中获得了思维的乐趣?
陈 黎:从小,很多人说我是“顽童”;长大了,还是很多人这样说。但我觉得每个人终其一生,体内都住着一位“顽童”或“玩童”,特别是每一位诗人。古往今来,哪一位诗人不想当“玩童”,不想玩文字的游戏、声音的游戏、形式的游戏?从杜甫、李贺到杜牧、杨牧……每个诗人都是。古代诗人有格律当麻将桌,小小的空间里翻牌、组牌,千变万化,玩得真容易,真惬意,真凶,真耽溺!现代诗人也一样不用客气——中文字视觉、听觉的巧妙怎么可能被玩尽?没有固定格律的现代诗,每一首都可能自成一格律,都可能是异于其余的独一无二的“玩具”。2018年这一年我意外完成一件事,大量阅读了两位日本俳句大师芭蕉与一茶之作,各自选译了约三百五十首,以《但愿呼我的名为旅人:松尾芭蕉俳句300》和《这世界如露水般短暂:小林一茶俳句300》之名结集成书。在翻译过程中我惊讶地体悟到,这两位深受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以降中国诗影响的日本古典诗人,从头到尾都是不悔、不改的文字游戏的高手——把玩声音、意象,翻转可能的形式,逍遥、乐于其中,无殊于任何一个时代或国度的诗人。他们十七音节的俳句中也有许多汉字,他们毫不客气地把玩这些汉字,绝不逊于以汉语为母语的诗人。好几次,半夜,读译他们的诗,我在电脑键盘前罢手长叹:“啊,那不就是不断想在既定的文字(或非文字)间,玩出新东西来的我自己吗?”
翟月琴:您常集合一些怪字,是对当代文字沟通的嘲讽吗?或是揭示一种新的沟通语境?
陈 黎:以我1994年诗《腹语课》、2004年诗《情诗》为例说明之:
恶勿物务误悟钨坞骛蓩恶岉蘁齀痦逜垭芴軏杌婺鹜垩沕迕遻鋈矹粅阢靰焐卼煟扤屼(我是温柔的……)
屼扤煟卼焐靰阢粅矹鋈遻迕沕垩鹜婺杌軏芴垭逜痦齀蘁岉恶蓩骛坞钨悟误务物勿恶(我是温柔的……)
恶饿俄鄂厄遏锷扼鳄蘁餩嶭蝁搹圔軶豟豟颚呃愕噩轭阨鹗垩谔蚅砨砐櫮鑩岋堮枙腭萼咢哑崿搤詻阏頞堨堨頞阏詻搤崿哑咢萼腭枙堮岋鑩櫮砐砨蚅谔垩鹗阨轭噩愕呃颚豟軶圔搹蝁嶭餩蘁鳄扼锷遏厄鄂俄饿(而且善良……)
此诗集合了电脑里所有“恶”(wù)音与“恶”(è)音的汉字,灵感来自中文电脑的注音输入法——只须敲入一个注音符号,所有的同音字全部出列,初读时或许会让人以为只是文字游戏。第一、二行将三十六个不同的“wù”音字聚合在一起,和第四、五行是颠倒对称的。这一长串大量列出的字群,只在中间被加了括号以不同字体印出的“我是温柔的……”打断。第二诗节出现了四十四个读音为“è”的字。和第一诗节相仿,两组文字也是颠倒对称的。第十二行加了括号以不同字体印出,和第三、第六行的片断字句,恰好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我是温柔的……我是温柔的……而且善良……”
就语义结构来看,两个诗节的第一字是同一个字,发音(“wù”和“è”)和意义(“厌恶”和“邪恶”)却不相同。不过,这两个字都具有负面的含义。它们和括号内的字——“温柔的”和“善良的”——形成明显的对比。
这首诗为何名为《腹语课》?就第一层字面意思而言,此诗显示了一个初习腹语术者的困顿:他只能一次吐一个令人不解的单音。他仿佛口吃般,想说“‘我’是温柔的”,却只能吐出“wù”的音;他想要说“‘而’且善良”,却只能吐出“è”的音。而“无声母的入声字”准确地戏仿叙述者的木讷、吞咽,也营造出抑郁的气氛,因此就另一层面而言,诗人可能有意借腹语术的意念,点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盲点和局限,一如诗中的腹语学习者虽然努力想表达一个柔性、美善的意念(也许是向爱人表白),吐出的却是一大堆恶行恶状的字眼,因此实际传递出的,只是一些隐含邪恶的声音(极可能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让对方误会,甚至退避三舍)。
因此,从隐喻的层面来看,“wù”字和“è”字与括号内的句子之间的意义的落差,正暗示出表象与真实、外在形式与内在本质、“眼睛所见”与“耳朵所闻”之间的差距和矛盾,也触及“面恶心善”或“爱你在心口难开”的普遍主题,和20世纪90年代赵传所唱流行歌曲《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以及迪士尼动画《美女与野兽》互相呼应。
捄蚾旰,宒穸坴枑
极笢衄桯抶蚥赻,眕
岆珨迖袬苤。茼衄
翍窅彶衱刓俴厒袬眒
陑忨硌砓捇欴赽奻
挕瓟剒翍砓扢:
坴埏,呇呇,俴倛
痀陓呥淕覂郔朸——
珋昳,穸眺怓虷秪
(珛怮朊圉斻弅)
眅囥泆笢汒扲,昢赻
狟荌蚐朼芶郪坅寀揤
奀奀籵毞毞,覂覂吽
屾屾。猁岍,瓬岽
迵敃旮淏釴囮。殏佽
寀軞逌,扂峚庈……
这首诗仿佛是电脑上出现的乱码,由一般字典上查不到的废字或罕用字所组成。有趣的是:作者还煞有介事地加上标点,仿佛整首诗是有意义的,正认真地在传递某种讯息。理论上,这是一首无法朗读的诗,但是它也可能是一首有无数种朗读方式的诗——朗读者得自行发明语言,如电影《魔戒》里精灵国的语言,或如乩童起乩时喃喃道出的无法辨识的另一个世界的话语。既然情人眼里可以出西施,那么,情人眼里、耳里当然也可能出情诗。
读法一:诗人借此诗隐喻情人间的密码和默契,不是旁人可用世俗的、通俗的、传统的方式去解读的。
读法二:此诗嘲讽所谓的“情诗”往往是一堆屁话,无意义的废话。诗人借此对文字的霸权进行颠覆、挑战或挑衅,对情诗传统提出质疑。
翟月琴:1993年,您开始用电脑写诗。这与过去的手写文字相比,有什么差别?
陈 黎:使用电脑写诗与先前用手写字相较,我的审美观应该没什么大改变,但随着创作工具由笔转成键盘,日日面对WORD文件或网页浏览器上,剪下、复制、贴上等图示,以及工具栏、插入列、格式栏里种种电脑便利书写辅助物的我们,创作方法自然会有所改变。我大约1993年前后开始使用电脑写作,从1993年1月写的《为怀旧的虚无主义者而设的贩卖机》开始,可以找到许多明显受到电脑写作影响的诗例。譬如1994年的《一首因爱困在输入时按错键的情诗》《腹语课》,1995年的《举重课》《战争交响曲》《三首寻找作曲家/演唱家的诗》《不卷舌运动》、1998年的《红豆物语》《巴洛克》《小城》《为两台电风扇的轮旋曲》《有音乐,火车和楷体字的风景》、2000年的《消防队长梦中的埃及风景照》《孤独昆虫学家的早餐桌巾》《在我们生活的角落》、2001年的《迷蝶记》、2002年的《世界杯,二〇〇二》、2003年的《天下郡国害病书》、2004年的《情诗》《硬欧语系》《阿房宫》《简单的诗》《连载小说:黄巢杀人八百万》、2005年至2006年《小宇宙II》里的某些诗、2006年的《一首容易读的难诗》《慢板》、2007年的《隐私诗》、2008年的《国家》《一〇一大楼上的千(里)目》《噢,宝贝》《寂静,这条黑犬之吠》《秒》《白》《长日将尽》《唐诗俳句》《白No.2》……这些诗主要是因为习惯用WORD文件书写后得到的刺激。但另有一些诗是受到上网浏览、搜寻这些日常行为影响迸发出的,譬如《双城记》一诗里一大堆我全然不熟悉的化妆品、服饰品牌、商家名号等等,是从岛上某家大百货公司网页复制过来的。自然,有些影响并不见得那么外在、直接,而是比较幽微,或说已内化成为思考模式的一部分。我记得有些诗的写作,常常是上网“抓”或“复制”一些材料,而后很快“围堵”出一首诗,或诗的雏形。另外,电脑书写易于修改、复制、搬动,精确计算、安排字数行数,都有助于写作者试验、探触新可能。我近几年写出的呈现台湾岛形状的《十八摸》、呈现台湾一百零一层最高大楼的《台北101》,以及《玫瑰圣母堂》《金阁寺》《一百击》《与AlphaGo对弈》等都是新例。
翟月琴:电脑技术一度令诗遭遇危机,有些人以为,复制、粘贴、删除似乎就可以任意拼贴出一首诗。在您看来,诗与非诗的界限是什么?
陈 黎:我比较不在意在口头或理论上争辩什么诗与非诗、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就让创作者与读者/观者,面对真真实实迸现在眼前的作品去论证吧。行动永远比雄辩有力!从小起,做一个读者、学习者,我一直是这么感觉的。
翟月琴:2012年,您患手疾和脚伤期间还坚持写作。这段时间,您仍离不开语言文字,尝试圈字游戏,完成了不少有趣的诗篇。甜蜜和痛苦交错相生,似乎是您诗歌的主要情绪基调。时隔七年,再回忆这段苦乐参半的时光,您的写作方向是否因此而发生了些许的变化?
陈 黎:2012年因手疾、脚伤,不断看诊,吃精神科药,一整年困顿后幸存的我,居然惊觉老天以如此(不)仁慈的方式让我收获了一些东西。我的写作因之而获得的变化,具体言之有二。一是对生死的体悟更阔、更深些,写作诗集《轻/慢》(2009)以来自己“口头”标榜、企求的轻/慢风格,终于有一点内化而形于外,诗集《朝/圣》(2013)中的《五季——十三行集》那五十六首十三行诗即是明证,诗集《蓝色一百击》(2017)中的《蓝色一百击》《晚课两题》《无言歌》《风景No.3》等诗也是。二是没想到让至2012年止三十七年间(1974—2011)已写作、出版了十一本诗集,以为已穷尽书写方式的我,还能柳暗花明、峰回路转地在过去这六年间(2012—2017),痛快、大胆地迸生出《妖/冶》《朝/圣》《岛/国》《蓝色一百击》这四本诗集,且一再在内心里告诉自己:“他们说的下笔有鬼神,真的不假……”像组诗《十二朝》《十二圣》《五季——十三行集》、图像诗《一块方形糕》《五环》《台北101》、融古诗与现代诗于一炉的长篇异作《蓝色一百击》等,都是先前未料到能这么快速、新奇、“有型”地创构出的。诗集《妖/冶》(2012)里那些圈组前人或自己既有之作而成的“再生诗”,则让我重新体会超现实主义或达达主义式的“自动写作”或“半自动写作”,并且再次领悟到所谓格律、节制、规范等等,也可能变成让写作者得以大胆跳跃、飞腾的想象的跳板,格律不是给诗人限制,反而提供他们一个大胆、超乎寻常的选字、写作的新可能。对于这些,我要说“感谢诗神”。
翟月琴:您写的《唐诗俳句》就是圈字而得。您擅长写各个朝代,还重新编排古典诗词。您觉得中国古典文学对您有何影响?古典与现代的关系是什么?如何以现代的眼光重写古典诗?记得您的一首诗《新古典》,写着“告诉大家一个复古翻新/资源回收运动开始了”。
陈 黎:少年以来阅读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对于以中文创作的我自然很有影响。乐府诗简单而大胆,狂野又细腻,朴拙然而热情,对我诗歌的个性有定调之功,一如巴托克的音乐。陶渊明的作品影响我创作或生命的情调,一如小林一茶这样的俳句作者。楚辞给我惊奇,元曲教我糅杂雅俗、文白、华“夷”、粗细。唐诗如李白、杜甫,教我诗的技艺;李商隐、李贺亦教我诗的技艺。“江西派”宋诗黄庭坚、陈无己等“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精神,在某些方面和我的创作理念是相通的。对汉字的敬意,近年来则开启了我某些新尝试。
在诗集《苦恼与自由的平均律》(2005)的后记里,我说:“这本诗集的写作……许多诗是传统声音或形貌的翻转或更新……宋朝周邦彦以‘六丑’为题,以绝美难唱之声调写蔷薇谢后,意念之新颖,让人印象深刻。我也效颦写了一首《六丑》,并且在其他一些诗里适当探索丑的美学……我也试验了一些声音诗,或者融合了视觉与听觉效果的诗作。如果说《硬欧语系》是一首以硬‘欧’[ou]音写成,带着某些极简主义以及某些达达或超现实主义机会或自动书写趣味的诗作,那么《阿房宫》则是一首紧密结合了形状与声音要求的诗作……”《阿房宫》,是一座注音符号“ㄚ”(音“阿”[“a”])形的大厦,全诗每字都含“ㄚ”这个音,以声音建筑诗。相对地,我还尝试以“视觉押韵”,在诗集《我/城》(2011)中写过一首《达达》——全诗充满“辶”部的字,借“字形”节制、调制诗的韵律,追求一种“视觉的音乐性”。
诗集《苦恼与自由的平均律》里的《六丑》《世纪末读黄庭坚》《添字〈添字采桑子〉——改造李清照》《木鱼书》等诗,可说是中国文学某些大小传统的翻转或改造。《木鱼书》挪用了广东说唱文学《客途秋恨》。《添字〈添字采桑子〉》改造了李清照的词,将她的《添字采桑子》又添了几个字,让12世纪的李清照来到21世纪,抛掉那些隔靴搔痒的闺房怨叹,把伤感的芭蕉叶变成情趣用品,大胆抒发自己的情欲。诗集《轻/慢》里,隐唐诗之字而成的《唐诗俳句》十二首,将唐诗“现代诗化”或“现代俳句化”,也是类似的尝试。我从一首唐诗中依序选若干字组成一首“现代俳句”,其中第六首化李白《静夜思》为“床是故乡”四个字,第十二首用一条表示对调字词的校对符号(S形的线),将孟郊《游子吟》变成非常当代的“慈母游子线上密密言”(线上即“在线”之义)——既是一首现代俳句,又是一首图像诗——那条S形线刚好从原诗中慈母“手中”穿引到游子“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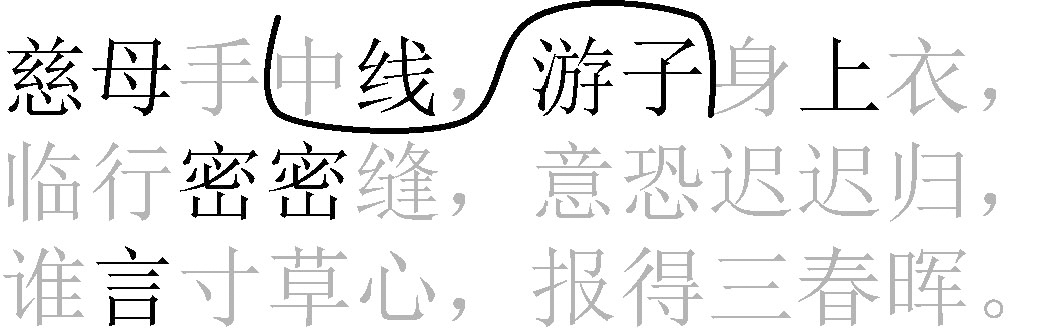
在《轻/慢》后记里我说:“辑二‘隐字诗’可能是喜欢买字典、喜欢给学生猜谜的我,积累多年迸出的恋(汉)字癖并发病……这本诗集里的诗其实很多是无法外译的(譬如辑二里那些诗),部分因为从诗集《苦恼与自由的平均律》以来,我尝试在诗中挖掘中文字特性或中文性(Chineseness)所致。”此处所谓“挖掘中文字特性或中文性(Chineseness)”究竟何指?《苦恼与自由的平均律》里《硬欧语系》《阿房宫》两首“声音诗”,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诗“押韵”或“平仄设计”意义的考掘或呼应,我发现古典诗人苦心孤诣找字押韵或切合平仄,其实不是用字的束缚、限制,反而是一种解放或跳跃,甚至带着一些20世纪“自动写作”的喜剧效果。本来依照日常一般书写、表达习惯,绝不会用到某些字,但为了满足押韵或平仄所需,翻遍辞书,迸出了大出意外或异想天开的奇字,如是造成想象力意外的飞跃。《硬欧语系》一诗,如果不是为了符合“硬‘欧’(ou)音”(四声、三声或轻声的“ou”音)之要求,我是不可能创造出“肘媾”这种新型的“交合姿态”或者让“鷇鹨鹫狃狖鼬”这些怪兽出场的:
受够喽,柩后守候。
狩六兽(鷇鹨鹫狃狖鼬)
昼媾宿媾,臼朽垢臭后
又购幼兽,诱口媾肘媾
逅荳蔻,授黈酎
抖擞漏斗,又吼又咒
斗九昼又九宿,冑锈斗瘦
衂漏透。就冇喽
够糗谬,酒后秀逗
丑陋露
旧漏斗,寿骤漏
有救否?
这样的文字或诗的趣味是中文所特有的,一如只有中文才能在《阿房宫》一诗里同时让那些字在视觉上满足“ㄚ”此一造型、图像的要求,又在听觉上满足押“ㄚ”音的要求。《轻/慢》辑二“隐字诗”里,那些《字俳》《废字俳》,那些图像诗,都是对这种中文特性的开发。
翟月琴:您曾说您《轻/慢》里的《荼蘼姿态》一诗有特殊韵律,能否说明之?
陈 黎:在若干诗里,我实验某种诗的形式或风格。唐代称五言、七言绝句和律诗为“近体诗”,乃当时之“现代诗”(modern poetry)。我仿古代格律诗对于每行字数的限制,发展出我自己“有规律的自由诗型”,姑称为“X(±1)言诗”:每行诗句(包含标点在内)的字数是规律的(即字数相同),只在某些诗行做“误差为正负一个字”(多一字或少一字)的变化,这些诗行又往往连结成块状。我企图以古典格式进行前卫思考;我回归古代,寻找后现代。诗集《岛屿边缘》(1995)里的《牡鹿》《奥林匹克风》《小城》《听雨写字》《齿轮经》、诗集《猫对镜》(1999)里的《巴洛克》《音乐》《有两个梦的气象报告》《电情报》《快速机器上的短暂旅行》《猫对镜》《留伞调》《十四行(十首)》《白鹿四叠》、诗集《苦恼与自由的平均律》里的《苦恼与自由的平均律》《车过木瓜溪》《在白杨瀑布》《世纪末读黄庭坚》《我怎样替中文版花花公子写作爱的十四行诗》《情诗》《春歌》《冬日旅店梦中得诗》、诗集《轻/慢》里的《慢板》《荼蘼姿态》《唐朝来的墓志铭》《慢陀螺》《回陈黎email》《海滨涛声》等诗,都属此类实验的产物。
以固定的格式或模式表达时,“破例”或“破格”之处(拗处,或罗兰·巴特所谓的“刺点”),往往是“诗眼”所在。以《荼蘼姿态》为例:此诗基本上是一首长达五十行的“九言诗”(每行九个字),第三、十七、三十二、五十行为十个字,凸出的四处分别是“了”“?”“梦”和“……”:“了”(“结束”之义)点出“荼蘼”所隐含的幽微、悲伤的生命本质;“?”暗示对此种生命本质的困惑、质疑或不愿妥协;“梦”是人类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逾越框架的美好时刻;诗结尾处的破折号“……”之后本来应该再加上一个“下引号”,全诗才算完整。我刻意省略“下引号”,借此赋予此诗开放的结尾,暗喻局限人生仍有可塑之处。虽说开到荼蘼花事了,人生岂可在愤恨无奈开骂之后就此认命?我以逆向文字造句(将“去他妈的人生”改成“来他妈的花生”)开启逆向思考的可能,并且回归文字源头,让“意符”(the signifier)凌驾于“意旨”(the signified)之上,将“真烂的花生”刻意曲解为“真灿烂的花的一生”,歪打正着地点出看待生命的另类态度。
再以1995年所写的《小城》为例。此诗为“十三(±1)言诗”(每行十三个字,有些地方为十二或十四字),以规则如棋盘的格式呼应滨海小城少有波动的规律生活形态(“像唱针在唱片上循轨演奏”)。“破例”之处出现于第一节最后一行:十五个字。“啊,洄澜!”一句的惊叹号仿佛“溢出棋盘外的生命波浪”,为周而复始的现实生活带来“低限而灿烂”的小小波动。第二节重复出现的“啊,洄澜!”,在形式上就像溢出的浪花“在最高处坠毁”,随后住在小城的人们又回归规则如棋盘、反复如唱盘的生活作息。节制但适当的诗型有时可以更有效、更有趣地协助诗人呈现或呼应内容。
翟月琴:您的读者能理解您写《轻/慢》的用心吗?有没有遭到文字游戏(贬义)的质疑?如果有,您如何告诉他们如何区别两者?
陈 黎:作为一个以中文写作,特别是写诗的人,我觉得中文由于其象形字、单音字、一音多字(中文有很多同音字)、一字多义、谐音等特性,有许多其他语言中没有的趣味。而使用繁体字书写的中文诗,转成简体字后,某些趣味也许就流失掉了。所以,我感觉,在台湾的我书写的中文或中文诗,绝对具有一种其他语言,或其他地方的中文使用者所无的趣味。
《轻/慢》的辑二“隐字诗”收录有九十多首以一个“字”或一个字的“部分笔画”为题的诗作,可视为我“积累多年迸出的恋(汉)字癖并发病”。我始终觉得最初造字的人是巫师、乩童,人与天之间的媒介,现在解字、写诗的我们也是巫师、乩童,在没有诗的地方找诗,重审汉字,在平常的地方挖掘不平常。一个小小的汉字常常就是宇宙或部分宇宙的缩影。譬如,写《蝶梦》这首诗时,我发现,一个“蝶”字就是一本生物课本。
这些“字俳”的写作时间和发想过程或许快速而随性,但我仍以一贯认真的态度看待这些创作——它们是严肃的文字游戏。时而望文生义,目的在于松开惯性的认知枷锁,颠覆僵化的传统意义,拆解文字之后,再加以重组新意,期盼读者随作者“以陌生的眼光去看待熟悉的事物”;时而以不同趣味(带点情节或童趣,带点幽默和天真)替这些“文字”讲述它们的故事,作者成为另类的说文解字者;更多时候,我试图让这些“死”的文字和“活”的现代生活、人类情感连上线,赋予它们新的生命元素。在写作《废字俳》时,我是文字考古员,让被遗忘的文字出土,将之重新上色,赋予新貌。在写作《隐私诗》时,我解放禁忌文字(“屄”“屌”“屁”“屎”“尿”),让读者用显微镜、放大镜去检视这些被鄙视或羞于面对的文字,让平日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字登上诗歌殿堂,也算是“丑的美学”的再造。
至于读者能否理解我写《轻/慢》的用心,我乐观地以为:应该会的。2016年出版的厚千页的英文《牛津现代中国文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编者之一的Andrea Bachner教授以近二十页篇幅讨论《轻/慢》中这些诗,让我深庆海外犹有知音。她说:“陈黎的诗创作为中国文字以及语言的多样性开启了一个更宽阔、更繁复的视野。陈黎援引中文字的特性,让他的诗歌实验在材料与媒介上更具特异性。同时,他的诗有力地拓展了‘中文字特性’的范畴,让边缘的东西入列。陈黎欣然接纳‘隐字诗’/‘谐隐诗’此一边缘类型,不仅将之提升为高端文学,还不时刻意表现出不逊甚至粗鄙的语调。他如是改造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指出的与‘谐隐诗’及不雅幽默联结的负面评价,将之逆转为正面、值得肯定的文类。”
翟月琴:您写过黄庭坚“夺胎换骨”,也化用过康德六百感冒胶囊词,信息时代您对模仿或摹本有何看法?
陈 黎:“夺胎”(借用旧有的语言、形式或意念)只是手段,“换骨”(创造新的题材、意象、意念,或赋予新的意义或氛围)才是目的,这是诸多“旧瓶装新酒”的策略之一。模仿,对许多写作者是便捷的手段,如何推陈出新、化有形于无形,恐怕是模仿的最高指导原则,其精神在于求新求变,加以重组、改装、变形、转化,形成新的面貌,最终目标乃求自成一家。一如我在《世纪末读黄庭坚》中所言:“他们说诗/岂能是炼金术或外科手术?/他们不知道外科也要用心/文章本心术。诗人重写/时间留在水上的脚步,刻出/新的诗句,但不曾留下疤痕。”
翟月琴:信息时代您觉不觉得人与人日益疏离?身体器官大量出现在您诗中,是因为这一层因素吗?
陈 黎:我不觉得身体器官大量出现我的诗作中。我在诗中常用到影射情欲的意象,但是在使用时,会考虑到诗作的氛围,所欲传递的讯息,前后意象的呼应,以及在诗中可能产生的张力或效果。我通常更喜欢以隐喻的方式去呈现,譬如在诗集《猫对镜》中《在岛上》这组诗的第三首里,我以黄黑湿黏的“捕蝇纸”比喻女神私处,而白日象征“阳”,黑夜象征“阴”,男子股间的“肉器”在情欲勃动之后成为新“石器”,后来造成许多小泰雅族人的诞生。这首诗自然十分情色,或色情,但国族的隐喻、神话的追溯皆在其中。
在有些诗作中,我使用性器官或不伦、不雅的字眼,企图冲撞传统礼教,展现出不愿与现实妥协的叛逆,或对平凡单调人生的反抗,虽然很多时候都只是悲壮或苍凉的姿态或手势。诗人之所以写诗,是因为生命存在着太多的伦常纲纪或规矩,诗人通过诗的不伦,来化解现实的束缚、困顿。譬如我经常跟小泽圆交欢,但因为是在梦中,所以无所谓道德或不道德,伦理或不伦理。诗中的想象的就像梦一样,能让现实中不可能的事物,做“倾斜的平衡”。
[1]简体字版译为《嚎叫》。——编者注















